
又是春天瞭,春天的小雨淅淅瀝瀝,一滴滴敲打在我的心頭……我的出生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我的上邊有六個姐姐一個哥哥,父母生到第六個時見到瞭哥哥,後又生瞭我的老姐,生完老姐,傢裡的日子日漸拮據,會做皮匠活的父親就和母親商量把傢從遼寧搬到瞭內蒙,說那裡皮張多,好做生意。搬瞭傢,母親就帶瞭環,可堅強的我還是讓母親偷偷地鼓起瞭肚子,我的哭聲喊亮瞭世界,卻喊走瞭父親。那年母親隻有三十六歲,最大的姐姐十七歲,三十六歲的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八人在異地它鄉相依為命。童年的記憶除瞭吃不飽,給我最多就是對春天與春雨的恐懼。“一到春天就揭不開鍋”,這句話我體驗很深。那時叫生產隊,生產隊是憑勞動力掙工分,我們傢沒有勞動力,出工的是母親,女人出工隻能掙一半工分,上秋分東西也隻能是一半,一方面是孩子多另一方面也是掙的少,於是全村缺糧最嚴重的也就是我們傢瞭。那時,每到春天村裡村外都能看到母親忙碌的身影,一筐筐的野菜就成瞭我們的救命糧。聽大姐說,挖野菜差點丟瞭四姐的命。那時傢傢都在挖野菜,村子周圍早已挖沒瞭。母親就趁星期天帶著幾個能走動的姐姐去山裡找野菜。開始九歲的四姐還是跟在母親身後,聽大姐一說“小根菜”好吃,四姐便貓著腰不眨眼地四下找著,一會便遠離瞭母親。太陽落山瞭,母親喊姐姐們回傢。卻不見瞭四姐。母親便扔下袋子跑上最高的山丘,以為四姐不會走遠。可即使母親喊變瞭聲,也沒見四姐。母親放聲大哭,脫下上衣包著發抖的三姐拼命地找著。不知走出多遠,躲在母親腋下的三姐猛的拽住母親,“媽,你看”。母親和姐姐同時看到瞭不遠處幾悚幽幽的綠光。“媽,是狼”,大姐也躲在瞭母親身後。如果說世界上的強者應該是孩子受傷時的母親,這話我信。母親發瘋的勇敢嚇走狼群,救出瞭四姐。丟瞭野菜的娘幾個回傢時,已是後半夜,而不懂事的我見母親回來就急急的張開小嘴咬住瞭母親那已經沒瞭奶水的乳,母親的淚水滴在我的小臉上而我卻全然不顧,姐姐們後來說,大傢都在哭,就我一個人一邊吃一邊抓住母親的另一個乳房不放。那時,別人傢一般時能吃上“凈面勃勃”(就是純玉米面的),我們傢就連一半面一半野菜的“菜勃勃”都不夠吃,母親總是趁我們上學後吃墻上長出的灰菜。一次,幾天沒進糧食的母親吃完園子裡的蔥葉後竟造成瞭胃穿孔,不得不手術。(這段文字我在小說《月兒彎彎》裡有過較細的描寫)都說春雨貴如油,我可沒那感覺。一則雖說春天點籽秋天收,可我傢也隻能收一半,二則是春雨不像夏天的雨水,來得快下得也快。真是“春雨潤物細無聲”,清一色幹打壘的房子就怕水泡,一場春雨過後不是墻倒就是屋塌,別人傢有男人,修得也快。我們傢就隻能靠母親一個人,而且還有一個擔心,就是鄰居那個“光棍”和村裡不安份的後生,於是隻要墻沒修好,晚上母親的枕邊就要放上菜刀,大姐那頭也要放上叉子。後來知道,其實也隻能是壯膽。等我也能背上書包走在春風裡時,對春天與春雨還是沒有好感。因為雖然單產承包解決瞭吃飯的問題,但大小八個孩子都要念書還是讓母親在春天裡發愁。記得,那時傢裡養瞭不少雞,除瞭哪個孩子生病母親是從不敢吃雞蛋的,八分錢一個,母親一攢就是一小筐。每年都能殺豬,卻很少能像樣的吃回肉。有一年,看我和老姐讒得不行,母親發誓要養兩頭豬,想著留下一頭給我們解讒。可還沒長成,因姐姐上學的事不得已就提前殺瞭。殺豬那天我和老姐連課都沒上好,半天時就跑回瞭傢等著吃肉。不想有一頭卻殺出瞭“豆”,不能賣,當母親決定賣那頭沒豆豬時,我卻爬在蛻瞭毛的豬身上死活不讓賣。印象中那一次母親第一次打瞭我,我還記得母親哭得很傷心。後來。母親對我們上學的事做瞭分工,大姐掙工資供五姐,二姐掙工資供哥哥,可我和老姐讀書就出瞭空檔,還得要母親解決。所以就是單產承包瞭,我們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太大的改變。母親就開始養牛賣,但還是不夠開銷。有幾年,一些小商販到村子裡收鴨絨、鵝絨,而且價格很高,母親像是看到瞭希望。經常到村頭、路邊去撿,有時母親會趟著齊腰深的水用自己制做的鐵勾子去勾水裡的絨毛。撿完瞭外邊的才撿自傢的。一次,也是一場春雨過後,放出瞭鴨、鵝,看到窩裡誘人的絨毛,母親勾瞭幾次後就吃力地爬瞭進去。鴨窩很小加上雨水浸泡,還是塌瞭下來,母親向外抽身體時,一顆釘在棚上的釘子在母親後背劃出瞭整整十幾厘米的口子,送到醫院,還是逢瞭十幾針。現在有時掀起母親的衣服看,就總有一種想哭卻哭不出來的滋味。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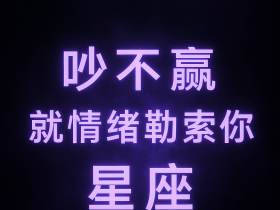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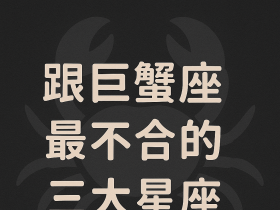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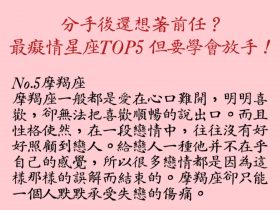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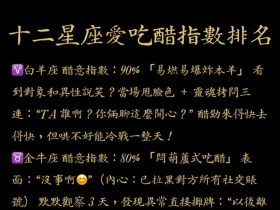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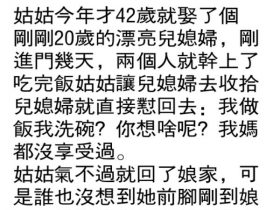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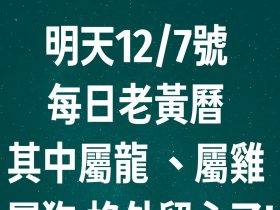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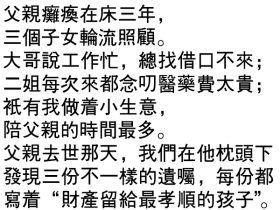

Leave a Reply